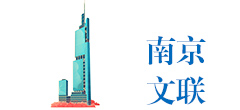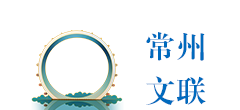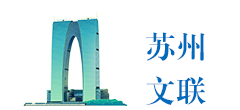摘要
非遗美学研究者已经从本体论、存在论、功能论三个向度深入地阐释了非遗审美价值,论证了非遗美学研究的合法性。作为基础理论研究,非遗美学目前还面临三个难题:一是要在美学原理层面讲清楚非遗审美究竟是康德式的普遍美感,还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各美其美”;二是要在关系层面论述非遗审美何以可能促进非遗保护;三是要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非遗美学走向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的可行性。非遗美学不仅要持续推进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非遗保护实践,把非遗及其保护实践视为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走向审美文化批评。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非遗美学,一方面可以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与方法,重点关注非遗日常审美经验的表达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坚持思辨的理念与方法,阐释非遗活态传承的社会心理机制——情感结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美学;非遗保护;审美文化;情感结构
作 者:季中扬,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作者简介

季中扬,男,1976年10月生,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首批文化艺术紫金英才。主要社会兼职有:农业农村部第二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人类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般项目、重大子项目等国家级项目4项,博士后一般资助、特别资助各1项,国家出版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学术著作4部,编著5部,主编10卷本丛书1套。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项目4项。
近十年以来,丁永祥、向云驹、高小康等学者先后提出从美学视角来研究非遗。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非遗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呼之欲出,诸如非遗的审美价值、非遗的审美特征、非遗美学与经典美学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都已得到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为什么要从美学视角研究非遗,究竟如何从美学视角研究非遗,诸如此类基础性问题却还没有得到厘清与系统阐述。此外,目前对非遗美学的讨论基本上都聚焦于非遗审美价值的阐释,以此论证非遗美学的学科合法性,而忽视了对非遗美学跨学科学术对话以及学术生长点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将致力于梳理非遗美学的发生轨迹,讨论其理论困境,阐述其走向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进路。
一、非遗审美价值阐释的三个向度
非遗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与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高度重视及保护实践密切相关,因而,不管是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还是法学、管理学的非遗研究,几乎都聚焦于“保护”问题。美学是一个以抽象理论问题为思辨对象的学科,很难切近非遗“保护”“传承”等具体问题,因而,在非遗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甚而可以称为显学之时,却没有进入美学视域。美学可以把非遗作为思辨对象吗?当然可以。非遗是产生于前现代社会,却又活态传承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非遗之所以能够进入现代生活,关键原因在于人们将其视为“遗产”。所谓遗产,必然是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站在现代立场对其进行价值发现与价值阐释。美学是长于价值阐释的学科,事实上,美学切入非遗研究也是从价值阐释入手的。
如果把非遗视为传统民俗的当代形态,那么,我们会发现,早在非遗概念产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在探讨非遗的审美价值了。赵德利从“美是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命题出发,发现人们创造人生礼仪、节日、民间文艺等民俗文化形式,表现出了感性生命的自由创造意味,这不仅使得这些民俗文化形式成为审美对象,而且,人们创造民俗事象本身就是一种体现生命本质的审美活动。非遗保护研究“热”起来之后,美学界仍然习惯于讨论民俗的审美价值。当然,传统民俗并不等同于非遗,非遗只是在传统民俗中被赋予了现代价值,被认为是值得保护、传承的部分。但是,恰恰是传统民俗固有的审美价值,让人们看到了其作为遗产的现代价值。事实上,非遗美学研究者正是看到了非遗本身具有审美属性,认为非遗审美价值是内在固有的,才将其视为美学研究对象的。王文章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存在的工艺品、表演艺术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是进行艺术研究、审美研究的宝贵资源。”丁永祥考察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现“侧重于审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除了传统医药之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另外九类非遗莫不与审美密切相关。他特别指出,诸如节日、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不仅其中艺术表演具有很强的审美性,这些习俗本身就是人们审美意识、审美情感以及审美理想的表现。向云驹进一步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非遗的价值标准具有重要的、主要的美学立场,“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如‘创作天才’‘艺术’‘文化形式’‘文化传统’‘文化史’‘灵感’‘文化交流之源泉’‘文化影响’‘杰出技能’‘活的文化传统之唯一见证’等,都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重要范畴、重要命题”。也就是说,非遗的审美属性与审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公认的,并非只有非遗美学研究者发现了它们。非遗之所以能够被相关组织通过特定制度与程序认定为非遗,其审美属性与审美价值是重要的因素。

新疆喀什土陶
基于非遗自身审美属性的审美价值看起来似乎是显性的、自明的,无需阐释。其实不然,在不同的美学话语体系中,非遗的审美价值甚至可能判若霄壤。经典美学并不认同非遗的美学价值,甚至并不承认民间艺术也是一种艺术。康德说:“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又说,“艺术甚至也和手艺不同;前者叫作自由的艺术,后者也可以叫作雇佣的艺术”。前者就像游戏一样,是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后者本身并不使人快适,是通过报酬而吸引人的事情。康德美学对手艺的贬抑是具有代表性的,已经形成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学传统。因而,非遗美学研究者必须建构新的美学话语体系,以新的美学原则重估非遗的审美价值。对此,笔者曾经提出,就中国美学传统而言,在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之外,还应高度重视来自本原哲学的“生生”美学,只有“生生”美学才能充分阐释民间艺术等“小传统”文化。立足于“小传统”文化的新的美学体系不仅可以弥补经典美学高高在上、忽视民众日常审美活动的偏颇,弥合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裂隙,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更为宏大的当代美学研究视域。正如高小康所言:“当美学传统和美学史的观念从主流精英文化形塑的经典之链中解放出来,审视整个社会审美活动中生生不息的活态传统,关注社会环境、文化群体、交往方式、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多方面生态要素的有机关系,就会看到远比经典美学体系更为复杂生动、更为广袤深厚的审美生态传承发展历史与当下生活的整合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小传统’美学开启的是比‘大传统’更大的美学传统视域。”
基于非遗自身审美属性阐释其审美价值,进而论证非遗美学研究的必要性,这是非遗审美价值阐释的基本向度。承认美是事物的内在属性,这是一种古老的本体论美学观念。接受过现象学洗礼的当代美学研究者,往往会从存在论角度看待审美对象,即以人的存在与对真理的追问作为理解审美与艺术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特性就是荷尔德林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脱它或漂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在海德格尔看来,审美与艺术并非为了使人虚幻地超越现实生活,相反,它们应该使人安居于此。正是从人类应然的诗意存在出发,非遗美学研究者发现了非遗更高层面的审美价值——“从现实来看,无论古今,人们确实都在追求着‘诗意栖居’,只不过不同的人群实现‘诗意栖居’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罢了。文人雅士追求‘诗意栖居’的方式常常是通过从事所谓高雅的艺术活动,如琴、棋、书、画、诗歌、小说等。而普通大众实现‘诗意栖居’的手段则是通过从事通俗的民间艺术活动,如民间传说、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戏曲、曲艺等”。高小康则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在讨论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时,是高度肯定人的劳绩的。因而,从存在论美学出发,不可能如同康德美学那样贬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审美与艺术活动的不纯粹性。相反,“‘诗意地栖居’就在于发现现实地、劳碌地生存于大地的诗意本质。这种发现不是剥离审美与现实劳作的关系,而是使美学回到人们‘一味劳累’地生产、劳绩的大地上,从现实劳作经验的深层发现、体验和升华出天、地、神、人一体的‘诗意’。传统生活技艺的重新认识、体验和传承就是在寻觅这种栖居于大地的诗意”。

高小康教授
除了从本体论美学、存在论美学出发阐释非遗审美价值之外,非遗美学研究者还从功能论角度发现,非遗在“遗产化”过程中可以衍生出某种新的审美价值。在非遗保护实践中,诸如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等,其审美价值是显在的、比较容易获得承认的,人们也往往由此确认其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但是,诸如柳编、手工制陶、手工印染等传统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由于失去了对其实用功能的需要,即使将其活态传承下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种民俗主义的表演。事实上,过去的日常生活技艺恰恰由于丧失了实用功能,其历经时光淘洗所积淀下来的岁月记忆才得以转化为充满情感的独特韵味,才得以成为人们审美体验的对象。正如高小康所言:“过去的生活历史在社会发展和历史传承中演变、凝聚、升华,转换生成了心灵化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一个文化群体特有的意象符号、地方性知识、想象力和情感体验,也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同时,传统社会中那些实用的日常生活技艺,其劳作方式在现代大机器生产与电子制造的对照下,焕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光辉,甚至已经转化成一种都市休闲体验方式。“做手工这种实践活动本身的意义受到了重视”,比如,在上海等城市不仅出现了诸多陶艺体验店,还有木工体验馆。在非遗美学研究者看来,各种手工艺体验馆的蓬勃发展,不仅意味着非遗得以创新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传统手工技艺的实用性已经成功地蝶变为“做手工”的身体美学的价值所在。

传统手工艺扬州漆器的制作
综上所述,非遗美学研究者已经从本体论、存在论、功能论三个向度深入地阐释了非遗审美价值,论证了非遗美学研究的合法性。但是,非遗美学研究就止于非遗审美价值阐释吗?在分析美学之后,尤其是在“美学死了”的语境下,究竟该如何研究非遗美学?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二、非遗美学研究的三个难题
非遗审美价值阐释仅仅意味着非遗可以作为美学思辨的对象,这只是非遗美学研究的发轫,要向纵深处开掘还必须解决三个基础理论难题:其一,要在美学原理层面讲清楚非遗审美究竟是康德式的普遍美感,还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各美其美”;其二,要在关系层面论述非遗审美何以可能促进非遗保护;其三,要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非遗美学走向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的可行性问题。
就上述诸家的非遗审美价值阐释而言,往往基于某些古老的美学预设,即事物具有某种审美属性,人们能够以一种“无利害性”的审美态度看待事物;即使人们的具体审美判断具有相对性,但是,我们还得相信人类有着某种普遍美感。然而,这些古老的美学预设在20世纪分析美学之后早已危机重重。
在18世纪,休谟(D.Hume)就明确提出:“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此后,美感论完全取代了美论。“无利害性”是近现代美学中美感论的第一块奠基石。正如杰罗姆·斯托尔尼兹所言,“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只要我们使用“审美”这个概念,似乎就很难否定“无利害性”审美态度。杜威曾试图批驳“无利害性”审美态度,他非常睿智地指出:“一个钓鱼者可以吃掉他的捕获物,却并不因此失去他在抛竿取乐时的审美满足。”事实上,钓鱼者之所以可能享有抛竿取乐时的审美满足,就在于他钓鱼时并不想着吃鱼问题,否则,就可能会处于焦虑之中。也就是说,利害关系其实是发生在钓鱼之后,钓鱼时仍然是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相比较而言,乔治·迪基对“无利害性”审美态度的批驳更切中要害。迪基指出,并不存在“无利害性”审美态度这样的心理状态,“无利害性”其实只是一个表明行为动机的术语。问题是,如果并不存在客观的美与“无利害性”的审美态度,那么,我们用来阐释非遗审美价值时的“美”与“审美”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呢?尤其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是,非遗之美究竟是来自特定文化传统,还是人们可以普遍感知的呢?很显然,人类保护非遗不仅仅是为了“各美其美”,这会导致过分强调文化身份认同,进而产生文化冲突,非遗保护必须指向“美美与共”。问题是,从美学原理层面来说,能够论证清楚“美美与共”的可能性吗?在美学思想史上,人们很早就开始讨论普遍美感问题。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ftesbury)认为,人们有着普遍美感,因为都有“内在的眼睛”。哈奇生(F.Hutcheson)也认为,人们的普遍美感来自“内在感官”。“内在的眼睛”“内在感官”显然是无法被证实的。康德就更换了讨论思路,他提出,由于美是无任何利害的愉悦对象,因而审美主体只能做这样的评判,“即它必定包含一个使每个人都愉悦的根据”,也就是说,“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不仅美本体内在地要求审美愉悦具有普遍性,而且审美主体的鉴赏力本身也要求这种普遍性。他说:“鉴赏判断要求每个人赞同;而谁宣称某物是美的,他也就想要每个人都应当给面前这个对象以赞许并将之同样宣称为美的。”这种推论性的、应然的普遍美感在人类的审美经验中并没有现实地发生。原因在于美作为无概念的客体,并非一种确定的、普遍的知识,审美鉴赏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只能是个人的、主观的。审美具有相对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如果没有社会与文化机制介入,审美很难达成价值共识。也就是说,从美学原理层面来看,脱离特定的文化语境,非遗的审美价值不可能因其自身而被人们普遍认知、认同。
接下来讨论非遗审美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与“打嗝”“被绊倒”等被动行为不同,非遗保护行动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其背后总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心理动因。行动因果论(Causal Theories of Action,简称CTA)主要倡导者唐纳德·戴维森(D.Davidson)在《行动、理由与动机》一文中提出,一个行动的理由正是由特定心理原因所构成,这心理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可能包括欲望、需求、冲动、激励和各种各样的道德观、美学原则、经济偏见、社会习俗等。也就是说,非遗审美可以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非遗美学研究者曾断言,“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曾经因为所保护对象的美学价值的全面高扬而使文化遗产保护广及全球,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品鉴、研究、欣赏、定位,也将极大有益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保护、弘扬”。但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必须是活态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传统而被理解与接受。可以认为,从理论上讲,非遗的审美价值很难超越“各美其美”的层面。如果作为心理动因的非遗审美价值无法达到“美美与共”层面,怎么能激发、保证对非遗保护行动的普遍共识呢?正如澳大利亚哲学家詹娜·汤姆逊在讨论审美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所言,“如果自然或艺术中的美只是在旁观者的眼中,那么审美判断就不会产生一般的道德义务······仅仅是个人和主观的价值判断无法让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欣赏某种东西,或者至少认为它值得保存”。非遗美学肇始于非遗保护实践,脱离了非遗保护实践,非遗美学就会沦为空洞的话语游戏,问题是,我们并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充分地证明非遗审美能够促进非遗保护。那么,究竟如何辩护非遗美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学术合法性呢?
美学是以思辨为其主要研究方法的,当思辨研究无法突破理论困境时,就会转向经验研究,在美学史上,审美心理学就是这样出场的。当纯粹思辨的方法无法解决非遗美学难题时,非遗美学是否有必要转向具体的田野研究呢?高小康曾经提出,非遗美学应该走向“民族志诗学”,“简而言之就是进入文化现场,去感知、体验、发现和‘深描’文化现场所呈现的审美意味”。有意思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者早已提出并践行了这样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王杰与海力波认为,“美学擅长对人类最精微、复杂、微妙的情感和思想作出研究、评价,传统美学的弱点在于缺乏实证基础,与此相应,人类学却擅长对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物质文化等方面作出研究,有一整套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的具体研究方法”。非遗本身就适合作为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的对象,民俗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非遗研究也大多采用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的方法。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是否可以弥补思辨美学的缺陷,破解非遗美学的理论困境呢?其实,国外学者很早就曾反思过美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问题,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然有助于在语境中以主位视角理解他者文化,但是,往往只能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很难实证分析人们的审美情感。正如弗瑞斯特(John Forrest)所言,美感“是个人的、内在的状态,众所周知,它是很难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得到充分了解的”。这也就是说,非遗美学走向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纯粹思辨的缺陷,切近非遗“保护”“传承”等现实问题,但是,并不能有效解决非遗美感共通性等根本问题。

作者在宜兴紫砂壶工厂田野调查,走访机车壶制作匠人
由于美学本身的复杂性,非遗美学难免面临种种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遗美学已经陷于困境之中,恰恰相反,非遗美学正是在直面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问题意识与方法论。当然,非遗美学还可以有更为宽广的视域,那就是走向审美文化批评,关注非遗的情感结构、语境重置、审美创意,及其日常审美经验的表达机制等。
三、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非遗美学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学就已经遭遇学科危机,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审美文化当然“不仅包括当代文化(或大众文化)中的审美部分,也可涵盖中、西乃至全世界古代文化中的有审美价值的部分”,但就其产生语境与问题意识而言,“审美文化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体现了现代性的重要范畴”,一般特指当代大众文化。在精英主义美学传统中,“美”“审美”“艺术”等经典话语体系通过强调非功利性、精神性、独创性,排斥了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与感官快感,建构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审美王国。审美文化研究恰恰相反,它“将审美置于日常生活的地面上,悬搁了经典美学自我设定的种种‘合法性’”;它“通过强调并肯定大众生活的感性经验事实,通过对现实本身的价值揭示,确立了‘回到日常生活’的立场,把精神的活动从超凡世界拉回到一个平凡人生的实际经验之中,从而反映了生存方式的日常化、生活价值的平凡化、大众活动的现实化,强调了‘世俗性’存在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完成了对于一种直接现实的价值把握”。概而言之,审美文化研究与思辨的经典美学不同,它面向当代日常生活,关注当代民众的日常审美表达、价值观念及其背后的支配性力量。正是在审美文化研究框架中,人们发现了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即“根据美的标准对日常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改造”。这一“改造”过程涵盖个人美容、家居装饰、城市景观等日常生活的外层,以及符号消费、媒介支配、网络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等日常生活的深层。我们发现,并非仅仅因为非遗保护政策的力量,恰恰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中,非遗通过彰显其审美价值才得以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这种审美文化现象需要美学的阐释与批评,尤其应该成为非遗美学充分重视的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第二届工作坊合影,南京,2022.3
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非遗美学不仅要重视当代美学转向的内在理路与学术脉络,还应该积极学习审美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提炼自己的核心议题。具体而言,不妨先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其一,跨文化实证研究视角下的审美普遍性问题。“美学这个学科就是建立在人们的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之上的。”审美普遍性问题不仅是美学的基础问题,也是非遗美学必须讲清楚的核心问题。在思辨美学史上,人们对审美普遍性问题一直莫衷一是。而审美心理学与审美社会学研究却表明,人类尽管在具体的审美判断方面差异显著,但这差异背后还是有某种普遍性的。尤其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表明,全世界人民在对自然美、人体美以及艺术杰作的欣赏方面体现出了高度的普遍性,这种审美普遍性可以从进化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识论等方面得到解释。审美人类学基于实证分析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人类的审美偏好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如果我们往更‘深’层次进行分析,或者做更‘高’层次的提炼,那么,可观察到的差异性也许最后被证明就是潜在共性在表面上所呈现的不同”。如果审美普遍性是可以实证分析的客观事实——尽管美学家未必完全赞同,那么,基于美学立场的非遗保护就有可能实现美美与共,建构一种可以实现人类共享的新文化。在此前提下,非遗美学研究也就获得了一种更为高远的学术理想,即如同审美人类学那样致力于面向全球的非遗研究,但不限于边缘的、弱势的族群文化,通过对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类非遗及其保护实践的实证分析与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反思与批判中寻求审美普遍性,探究人类非遗交流与对话的学理基础。
其二,非遗的审美创意转化与日常审美经验表达机制问题。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下,非遗通过创意转化,突破地方性、历史性局限,成为可共享的当代审美文化,这是非遗审美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其实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审美资本主义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解了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例如,对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来说,玛丽莲·梦露头像、32幅金宝汤罐头图像、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而且无所谓原作,可以复制、量产。当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之后,也就没有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界限与区隔,非遗也就可以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对象。事实上,在古村落、都市中的传统街区以及网络等文化消费空间,非遗已经被广为接受,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品之一。与一般大众文化不同,非遗来自传统,不可避免地具有地方性与历史性局限,只有通过创意转化赋予其现代意味的审美性,才能消除其地方性与历史性局限,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都认同、接受。这看起来似乎与非遗保护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其实不然,非遗保护宗旨恰恰强调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通过审美创意消除非遗历史性局限并非要完全清除其历史因素,而是以现代人的目光重新审视其历史因素,真正活化其传统因子。事实上,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内在要求。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后现代主义倾向于“恢复过去的文化”,试图“找回已往的一切文化,找回所有被摧毁了的东西”。所谓非遗的当代审美创意,的确不是为了原汁原味地保护非遗,它本质上就是对传统摧毁之后的重建,是混合着记忆与怀旧的情感,生产出的符合当代大众口味的审美文化产品。

都市中的传统街区:南京夫子庙步行街
其三,非遗活态传承的社会心理机制——情感结构问题。非遗是重新进入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过去的文化形态,是一种被选择的传统。面对过去时代及其文化,我们只是挑选、强调了其中某些因素作为一种历史沉淀物来认识。事实上,“在它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种要素都是溶解的,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面对这些被选择的文化因素,我们似乎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而缺乏活生生的感觉。如果是这样,新一代人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前一代人的生活与文化,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活态传承的非遗。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R)却发现,新一代人完全能够理解前一代人的生活与文化,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共同的“情感结构”,新一代人的“情感结构”虽然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保持着连续性。所谓“情感结构”,是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须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正是通过它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传承,我们才能对过去时代及其文化感同身受。其中的“结构”是指独具特征的文化模式,“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对于非遗的审美文化研究来说,“情感结构”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概念工具。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非遗并非碎片化地散落在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只能在审美资本主义逻辑下作为文化资源被利用;非遗是一种活的生活文化,是充满感性的情感体验的对象,可以被后人从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层面理解、接受。此外,这个概念还有助于深度解释非遗的当代文化功能问题。一般认为,非遗作为特定群体共享的传统,可以唤醒集体记忆,而“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问题是,非遗为何能够群体共享,能够唤醒集体记忆呢?关键就在于一代代人有着共同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既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又能够保持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
综上所述,非遗美学由思辨研究走向具体的审美文化研究不仅可能在实证研究层面重新论证审美普遍性难题,为非遗美学研究夯实理论基础,而且可以推进非遗美学研究转向“文化批评”,揭示非遗保护与利用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支配性力量。此外,以“情感结构”为核心概念,非遗的审美文化研究还可能在“批评”之外重构正面阐释的研究框架。
图片
结语
从传统美学视角来看,大多数非遗都具有审美价值,即使是传统节日等民俗活动,甚至是中医药、珠算、二十四节气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也都蕴含着审美的情感与想象,完全可以作为美学研究对象。正是基于传统美学视角,非遗美学研究者分别从本体论、存在论、功能论三个向度深入地阐释了非遗审美价值。但是,基于传统美学的非遗美学很难解决三个难题:一是如何在美学原理层面讲清楚非遗审美究竟是康德式的普遍美感,还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各美其美”;二是如何在关系层面讲清楚非遗审美何以可能促进非遗保护;三是如何在方法论层面论证非遗美学走向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的可行性。
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当代美学走向了审美文化批评,它不再局限于艺术哲学,“它的结构应该是超学科的”,或者说“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平行的理论话语共存的广阔领域”。在当代美学观念中,非遗保护是一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可以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对象。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非遗美学,一方面可以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与方法,把非遗进入当代日常生活视为审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与“景观社会”的突出表征,重点关注非遗创意转化及其日常审美经验的表达机制,分析非遗资源化、审美化、民俗主义化等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性地思考审美普遍性、非遗活态传承的社会心理机制——情感结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