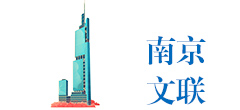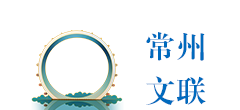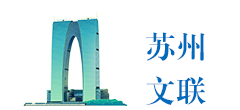常州道情,源于“说因果”,是民间艺人于农闲时走寸串户说唱劝人向善的顺口溜和故事,后取“说情道理,惊醒顽俗”之意,故名“道情”。
常州道情由上下手两人联档演出。上手称“大先生”,承担所有说表唱做,手上道具有醒木、折扇、三跳板。下手称“小先生”,一般由徒弟担任,专事打扁鼓、击檀板,以及唱帮腔“拖下板”。唱腔曲调以长三调为主,平调、阴阳调、悲调等为辅。
道情兴盛时,常州“四城门八水关”所有的茶馆都爆满。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百年的常州道情,是常武及周边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
有史可查最早的常州道情艺人,是咸丰年间武进县的周天瑞。周天瑞收徒薛良荣、张金富。民国初年,张金富的徒弟刘全海把道情从农村带进城市,缔造了常州道情的全盛期。薛良荣的徒弟屠产法则留守农村,以武进小新桥为据点,自成一派。之后常州道情的传承谱系都从刘全海和屠产法两支延续而来,其中刘全海、刘银生(屠产法徒弟)、张忠芳(刘全海徒孙),并称为常州道情“三状元”。
三状元:刘全海、刘银生、张忠芳
1914年,张金富的徒弟刘全海在农闲时进城卖艺,踏出了常州道情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刘全海从小没念过书,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师从张金富后,完全靠死记硬背接了师父的衣钵,满师后即在武进各茶馆与人合伙开唱。他口劲极好,吐字清晰,能掌握抑扬顿挫之法,操纵转折起伏之妙。说表上,每于慷慨激昂时,力如喷泉;于悲凉凄婉处,又哀若孤鸿。唱调上,擅长长三调、一六调,嗓音脆亮圆润,无论快慢疾徐、高腔低调,唱来皆有韵味,更能数十百句一气呵成,从不忘词丢腔。他的这套本事在同行中无人能及,被誉为“不识字状元”。
刘全海进城后,先是在城隍庙摆摊唱道情。他自编自唱长篇《杨家将》《金鞭记》,以半小时至40分钟为一回,每到紧要关目处即暂停,向观众要钱,艺人行话“散扦”。刘全海能根据不同观众随口编“散扦”唱词,见谁就唱谁爱听的彩头话。“散扦”过后,便接着说唱,或由徒弟换唱。如此唱过便散,散过再唱,一直从午后唱到黄昏收摊。如果这时观众听出瘾来,不肯散场,则可再唱,称为“拔书”。有时刘全海的“拔书”竟然一拔再拔,直至点起蜡烛,唱到半夜。
刘全海打出名气后,在老西门独资开办留芳茶店,偕徒弟开业说唱。受刘全海影响,武进农村的道情艺人纷纷进城,遍布各大茶馆书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常州道情的演出人员有150多人,以常州为中心,流传至宜兴、溧阳等地。从业人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其中难免鱼龙混杂,出现恶性竞争,使得艺人们感觉有必要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加以引导约束。1932年,常州道情艺人成立“新裕社”,公推刘全海为社长,地址就设在留芳茶店,一年聚会两次,点香烛拜祖师。刘全海拟定了详细的社规,用来规范艺人,如:
无师不准入会,入会需由同行艺人介绍,会员通过;
不许欺师犯上,不许戳壁脚,不准赌钱,不准白相女人,不欠码头债,违者轻则当众警告,重则打屁股,开除会籍;
倡导艺德,艺人互相尊重,互相引荐,介绍场子,对外地艺人初来行艺者管一宿两餐,无收入者离去时给予路费……
新裕社的成立,标志着常州道情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它改变了以往艺人个体行为散漫和草根的面貌,以行业群体的约束力对艺人的从业资格和职业操守进行了规范,通过师徒相授的途径,试图营造一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行业格局。这种行业组织行为对内增强了艺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对外巩固了整个行业的地位,使常州道情成为民国时期江南的重要曲种。
通过新裕社的经营,刘全海显示出了他在组织管理上的才能,个人声望达到顶点。但刘全海性情豪爽,喜交四方朋友,挥金如土,不留积蓄,以致老年时生活潦倒,靠徒子徒孙接济勉强度日,最后死于贫病交加之中。他的大徒弟徐继昌接掌了新裕社,徐继昌木匠出身,资质平平,演出市场很快被武进小新桥屠产法的一支抢了去。
屠产法能咸鱼翻身,全靠收了个好徒弟刘银生。刘银生只有一只眼,身体孱弱,说起书来没有冲劲,气氛沉寂。但屠产法慧眼独具,看中了刘银生有些许文化功底,是个创作型人才。刘银生对书目肯钻研,讲求故事逻辑,常有个人见解,表演时娓娓道来,一唱三叹,场面虽不热闹,却耐人细品,是路阴功,被誉为“阴间状元”。然而刘银生因为身体太弱,三十多岁就病亡,未能继续对刘全海一系形成冲击。
刘全海死后,接班的徐继昌虽无才华,但也兢兢业业,苦心经营,把新裕社交到了下一代手上,留给徒弟张忠芳发扬光大。张忠芳另辟蹊径,在演出中插科打诨,诙谐幽默,曲尽其妙,被誉为“滑稽状元”。外加他有一副好嗓子,唱阴阳调独树一帜,嗓子一开,满座倾倒。看家书目为《隋唐》,以程咬金为贯穿人物,增删取舍,自编成书。张忠芳以近现代社会世态、人情冷暖、民风习俗以及各种笑话趣谈融于程咬金一身,使其形象不仅粗莽可爱、耿直活泼,而且具有正义感,深受听众欢迎。张忠芳在留芳茶店连说18年,盛况不衰,无数学徒争拜张氏门下。但张忠芳也与当时许多艺人一样,有了钱后便染上赌博恶习,终至欠下巨额赌债,只身逃亡上海。在常州有他的“铁粉”,托上海的青帮大佬出面摆平赌债,张忠芳得以回乡,继续唱道情。经过这番起起落落,张忠芳身体大不如前,在一场演出中,说到紧要处,拳脚并举,喊声如雷,引发脑溢血,猝死台上。张忠芳的过早逝世,是常州道情的一大损失,常州道情原有可能在他手上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便再无这样的机会出现。
三响档:张唯一、张荣生、顾友梅
张忠芳死后,他的继承人有张唯一、何云奇、曹寿林、丁鹤龄、顾友梅、许玉泉等。张唯一是张忠芳的儿子,继任新裕社社长,坐镇老西门留芳茶店。其余徒弟一部分转入农村,形成两派,号为“西乡帮”和“东乡帮”。西乡帮以何云奇为首,在孟河一带演出;东乡帮以顾友梅为首,在武进一带演出。顾友梅13岁从张忠芳学艺,满师后与师兄曹寿林搭档演出,看家书有《华丽缘》《珍珠塔》等。他的说表清晰细腻,唱腔高亢激越,唱功用韵精熟,十八个道情韵脚均能随时换用。拿手好戏“两头红”,从太阳落山一直唱到日出东方,一韵到底,不走调,不出韵,堪称一绝。他还借鉴吸收了摊簧、评弹的长处,用来丰富道情的唱腔。
就在张派子弟各立山头时,武进屠产法的小徒弟张荣生杀进常州城,与张唯一打起擂台,使得竞争局势更为激烈。张荣生是武进长沟村人,16岁给屠产法当下手,18岁在武进各茶店单独演唱。1946年,张荣生在常州东门外悦和茶店演唱《玉蜻蜓》《万年青》《金台传》等曲目。他唱平调、长三调最拿手,说表多用武进的村巷俚语,每以乡言、农谚和风土习俗穿插,自然贴切,如谈家常,令听众耳目一新。张荣生和张唯一分别占据常州东西两厢,连续演出十年,天天客满,长盛不衰。这是继“三状元”之后的又一个兴盛期,张唯一、张荣生、顾友梅被誉为这一时期的“三响档”。然而他们都被眼前的盛况迷惑,对于书目建设缺少长远打算,现炒现卖,演出质量日益下滑。到了他们的徒子徒孙辈,基本功薄弱,会唱的越来越少,已不知曲调为何物,索性拿掉唱段,全改为说。道情逐渐变成评话,这门艺术的特色也就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道情艺人为主体,建立了常州市曲艺联谊会,顾友梅任主任,协调组织包括道情、宣卷、小热昏在内的演出事务。顾友梅意识到整个道情行内唱功的缺失,组织艺人对传统曲目进行挖掘记录,整理出开篇、唱段六十多个。顾友梅自己整理的传统短篇《小八哥告状》,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获优秀奖。然而留给顾友梅的时间已然不多,紧接着历次运动,常州道情团体解散,艺人改行,所存资料、曲本大多被毁,常州道情遂告失传。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三响档”之一的张唯一有个小徒弟,叫周玉峰,先唱常州道情,后学苏州评话,又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完善了常州评话,三次获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成为一代曲艺名家。常州道情虽已成遗存,但它开枝散叶,其血脉仍以常州评话的形式代代流传。

作者:言禹墨
来源:江苏省曲艺家协会